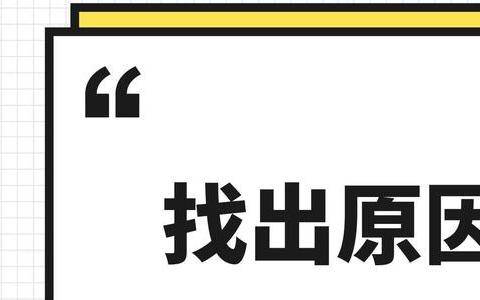很抱歉,今天的推文不是關于營銷的。這是我大學時期所寫的舊文,有人覺得有價值,有必要把它發出來。我想了下,就把大學時期所寫的文章做一個集合放在今天的推文上,算是一個懷念吧。
大學四年,可能什么都沒學會,但是讓我找到了求知的本能,終生受益,很感謝。
洛克說過,人生而平等。
盧梭說過,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權力的誕生(分工的結果)
自由與平等是人類世界的兩大理想,可以說,人類文明的程度就是自由與平等實現的程度。為了實現這兩大理想,人類社會不斷地追求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說過,分工帶來經濟發展,越精細的分工越能促進經濟發展。同樣的,在社會學上,權力的誕生也來自于分工,但是這種分工越精細卻越導致等級與壓迫。
在原始社會,人們的食物主要來自于采集和狩獵,女人負責采集,男人負責狩獵。通常下,采集來的食物要比狩獵來的獵物更多且更穩定。
但是,在原始社會,人們生活在部落里,各個部落面臨嚴峻的生存競爭。男人狩獵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取食物,而是為了加強鍛煉以抵御其他部落人員的攻擊以及應對自然災害。部落里有了這樣一支兵強馬壯的隊伍就不怕其他部落的攻擊。
這就像現在世界中,各國對于國防事務的開支,在國防事物開支越多,防御能力越強是同一個道理。一個是付出的是食物,一個付出的是金錢。然而站在人民大眾的角度來講,這種不生產的支出必然減少人們的生存或生活福利。這種男狩女采的簡單生存方式是很和諧的。
從采集狩獵社會進入農業社會,糧食可重復生產,周而復始,而且產量增大,糧食的生產足以養活所有的男人女人,狩獵得來的食物變得可有可無,而且在這時農業與狩獵不能并存,因為農業的種植在于平原、土壤肥沃的地方,而狩獵的森林遠離農地。
在這種情況下,狩獵獲取食物的途徑變得難以可能也無必要,就是剩下守衛領土保護家園這個職責。在這樣的進化當中,狩獵的不生產的人成了農夫的、生產者的保護人、管理員,也就成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權力也因此而誕生,壓迫也因此而產生(注:已經有人指出這里推斷是有問題的,具體哪里問題,你們可以在底部留言。這是很久之前的舊文,我也就不修改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權力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不平等與壓迫的開始。人類文明的進程就是權力與反權力的斗爭,個人權利與專制權力的斗爭。
血統論(模式:牧羊人—羊)
權力誕生之后,階級開始分化,掌握權力,行駛管理權力的人員也就必然要開始溫飽之外的享受,他們不僅要吃的好,還要穿得好,住的好,行的好,而吃穿住行樣樣要好,就必然導致社會分工的加快,因此古代城市的雛形就開始形成。因此,權力集中的地方就是城鎮興起的地方,不再是簡單的村落了。
權力經過長時期的完善和發展,逐步開始建立起一系列等級森嚴的秩序。中國從封建社會進入中央集權的社會。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大一統的王朝,以血統為核心的皇權世襲、貴族世襲成為權力的傳承方式。
套用物理學里的能量的守恒原則,以血緣為基礎的權力也是守恒的,這種權力不會消失、不會轉移,只會拓展、延續下去。也就是說,人一生的命運就在你出生的那一刻決定。在高度集權的社會里,權力意味著一切,出身皇族、貴族意味著你擁有永恒的權力,便擁有了地位、榮譽和金錢。
而如果你是出身于底層草民,那么你一生就注定就是被壓迫的命運,不能反抗,無力反抗、只能屈從命運的安排,希望下輩子出身于一個好家庭。
對于國家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系,我們常常用牧羊人—羊的模式來解讀,以血統為核心的權力傳承方式就是典型的“牧羊人—羊”的模式。
在這樣的模式中,被統治者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沒有任何權利,沒有任何自由,沒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有的只是生不如死的活著,羊的唯一權利就是長肉的權利,你必須勤懇的勞作,兢兢業業,為統治者創造物質財富。而對于統治者而言,也就是牧羊人而言,他有處死羊的權力,被皇上處死也得感謝隆恩。
而對于傳統中的帝王之術,無非就是控制牧羊人與羊之間的關系。牧羊人不能把所有的羊都殺掉宰掉,因為殺掉所有的羊,牧羊人以后就沒得吃了,自身的生存就成為問題。但是,牧羊人也不能讓羊過的太舒適,不能養的太肥,一旦養肥,羊就會開始不聽牧羊人的話了。因此,帝王之術要義就是讓羊不胖不瘦,讓草民不死不活是最好的狀態。
科舉的改造(模式:牧羊人—狼/狗—羊)
東漢以來,劉秀建國后大封功臣,導致門閥士族興起,門閥制度開始盛行,至南北朝時期,達到高峰。這些門閥士族的大地主、大豪強的實力逐步擴大,對政治、經濟的影響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就連皇帝也忌憚三分。
隋唐之前,人才的選拔是通過地方官員的舉薦。舉薦制度的關鍵在于舉薦者的人品,但是由于門閥貴族買通舉薦者,錢權交易使得舉薦制度變得不可持續,門閥士族的勢力不斷擴大,皇權衰微。
隋唐時期,為了鞏固國家政權,當政者大力打擊門閥士族,為提拔寒門之士,而采用科舉制度,科舉的興起,促使了門閥制度的沒落。科舉是一種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直接催生了不論門第、以考試產生的“士大夫”階層。
16至17世紀,中國的見科舉取士制度傳到到歐洲。
18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19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后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今天的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從權力的角度來看,科舉選士制度的偉大不在于它的公正,而在于科舉打通上層與底層之間的通道,使得權力的獲得不再是唯一與血緣相連,使得各個階級開始流動,使得出身不再是唯一獲得權力的唯一來源。
底層人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權力的中心,改變自己的命運。即使這種追求幸福的權利仍然是通過權力來實現的,但是依然不可否認科舉的偉大之處。
而對于統治者來說,科舉制度不是讓底層人員來分享皇權,只是賜予這些人以某些權力來管理自己的帝國。畢竟對于皇權來說,官權只是一時的,有限的;對于王朝的普羅大眾而言,官員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
以血緣為基礎世襲的皇權貴族權力傳承方式加上以后天努力為基礎的科舉選士的官權構成了權力新格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這種新的權力格局才造成兩千多年中央集權的穩定。
而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方式來看,統治的模式從“牧羊人—羊”轉變為“牧羊人—狼/狗—羊”的模式。
對于只受皇權限制不受人民限制的官權而言,官員對于皇帝只是一條狗,而官員面對老百姓就是狼,狼的本性必然要侵害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官員的本質是貪婪。所謂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皇權的高度集中必然最終導致王朝的沒落,直至被另一個皇權所代替,這就是所謂的“黃炎培周期律”。
而每個王朝的建立者都想像著想秦始皇那樣建立不朽的萬世的帝國,像秦始皇、秦二皇、三皇……因此每個朝代的建立者都懂得帝王之術,都懂得如何建立牧羊人與羊的關系以及狼與羊的關系,早期的牧羊人必然要給狼圍上一條鐵鏈或者給羊群圍上一層圍欄以防止狼無休止的侵害羊群、導致皇朝的衰落。
而隨著皇朝的發展,后繼者已忘記太祖的警戒,忘記了狼的本性或者說不管羊的死活,只顧自己的荒淫。而不受皇權限制的官員必然顯露出狼的本性必然要侵害羊群。
而對于中國傳統中的清官情結,本質上是一種狗文化。清官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他只對皇帝忠誠,雖然他自身去除了狼貪狼的本性,不會去侵害羊群,但是他永遠不會意識到主人的不正當性。
草根才子杜君立在其博文《中國的狗文化》說道:中國人最愛說“狗是忠臣,貓是奸臣”,言者實則把自己當成了皇帝,這是一種典型的下意識。皇帝驅使官吏如同轟狗,官吏喪失人格而取“忠臣不事二主”之狗格,盡其“犬馬”之勞,與中國狗文化如出一轍。難怪中國民間一般將“普通老百姓”的“父母官”常常稱作“狗官”。倒很少有其他“狗人”或者“狗民”的說法。許多時候,官場的貪腐丑聞之所以曝光,也是“狗咬狗兩嘴毛”的場面。
市場的力量(突破權力的新途徑)
清華大學社會學家鄭也夫教授在《信任論》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中國通過科舉走上了考試競爭的道路,西方則通過商業走上了市場競爭的道路。如果說,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從權力內部打通了上層與下層的流動,那么西方的市場競爭道路則從權力的外部開始突破。
中國傳統社會里,商人是最沒有地位的,“士農工商”中商是排在末位的,重農抑商一直作為國策。雖然中國在很早就有完善的錢莊制度、在宋代就有紙幣“交子”的出現,但是商業從來沒能夠整合起一股強大的力量,資本的力量在權力的控制下只能有限度的發展。
權力的死敵是自由,無論這種自由是人身自由,還是思想自由。由于商人的流動性,不穩定性,難于管理性,從大一統王朝的建立開始,商業一直受到當政者的控制。一個商人即使賺到了很多錢,他也只能回到老家買地、建房成為大地主或者買官、做官往仕途上走。商人的資本不允許擴大再生產,這就阻礙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與統一王朝的大中華不同,歐洲從來沒有被統一過,這也許是阿爾卑斯山的功勞,導致了歐洲各國的封建制度遲遲未能進入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也可能是基督教教權對于皇權的限制,使得權力制約權力;還有可能是地理大發現的導致全球爭霸事業的開始,導致歐洲商業的興起。
18世紀,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出版其傳世之作《國富論》,“看不見的手”開始指揮社會的運作,從此開啟了商業時代的輝煌。重金主義、重商主義的思想被統治者接受,資本成為權力之外的另一種強大力量被權力所接受,并且逐步瓦解權力賴以運作的基礎。
可以說商業的發展,促進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發展,最后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建立資產階級政權。商業的興起與發展,其貢獻不僅僅是經濟水平的提高,國民財富的增長,更為關鍵的是它使得人們不再關注唯一權力途徑,它使人們可以在權力體系之外獲得另外一種成功、另外一種尊敬和榮譽。并且以資本利益為一體的共同體突破權力的包圍,使得西方走上了資本民主的道路。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第三次浪潮》中說過,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促進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亨廷頓的在書中的觀點在中國得以嘗試。
20世紀80年代,中國結束了長達三十年的閉關鎖國之后開始進行經濟改革,這種經濟權力的下放權力,導致中國商業經濟的蓬勃發展。30年來,GDP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長,中國財政收入不斷增長,國民生產總值躍居全球第二,僅居美國之后。中國無疑創造了奇跡的增長速度。
然而,在經濟發展、GDP增長的背后,政治民主化卻遲遲未啟動,只見雷聲不見雨點。經濟上的市場化和政治上的權威化,必然導致權錢交易的盛行、公民的自由無法保障。經濟的發展未能實現亨廷頓所說的經濟自由帶動政治民主化,相反的,權力開始作為一種商品在市場的邏輯之下與資本結合,打擊民眾的自然權利和自由。
權利的邏輯(模式:鎖在鐵籠的狼/狗—公民)
美國前總統布什曾說:人類五千年來最輝煌最為值得驕傲的是,把統治者關進了鐵籠。只是可惜,把統治者關進了鐵籠的國家太少太少。太多國家的統治者,猛過老虎,狠過豺狼!
戈爾巴喬夫與薩哈羅夫站在一起,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他說:”對于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
如果說文藝復興是從神的束縛中把人性解放出來,使得人成為價值實體;那么,啟蒙運動就是把人從權力的而束縛中解放出來而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思考價值的公民,國家權力這種怪獸“利維坦”被送進鐵籠里,實現了個人的尊嚴。正如愛因斯坦所言:“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國家應是我們的仆人;我們不應該是國家的奴隸。”
與權力時代不同,在權利時代,國家的作用不是經濟發展、不是GDP增長速度、不是道德建設、不是追求真理與知識、甚至不是富民強國,國家的作用只是保證公民的自然權利不受侵犯,維護公民享有自由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如果前者成為國家的目的,那么,這個目的將吞噬個體的自由和幸福,違反人們建立政府的初衷和目的。因為在國家權力這個“利維坦”面前,個人的反抗微不足道。
在權利時代,與權力時代的“牧羊人—狼/狗—羊”的模式不同,統治者被關進鐵籠里,這鐵籠用權力制約、民主選舉、新聞監督和憲法保障而鑄成。羊群也經過社會啟蒙或自我啟蒙成為憲法保護下的公民。這里的模式變成了“鐵籠里的狼/狗—公民”的模式。
美國《獨立宣言》對“自然權利”作了這樣解釋:“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有從他們‘造物主主’那邊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日裔美國政治學家福山在1989年發表了“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
但現實遠不是如此。
原創文章,作者:營銷學習社,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kmwhg.com/891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