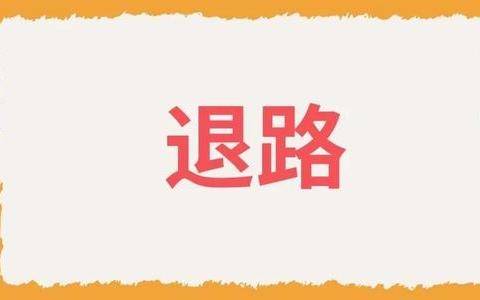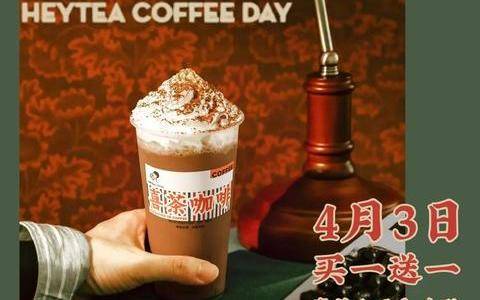很抱歉,今天的推文不是關于營銷的。這是我大學時期所寫的舊文,有人覺得有價值,有必要把它發出來。我想了下,就把大學時期所寫的文章做一個集合放在今天的推文上,算是一個懷念吧。
大學四年,可能什么都沒學會,但是讓我找到了求知的本能,終生受益,很感謝。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在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上語驚四座。這段話被參會嘉賓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轉發3.5萬次。
中國是不是一個精英治國的國度呢?我以前認為是的,科舉是精英治國的象征,是一種通過嚴格考試選拔出來的一種儒家精英。他幫助皇帝管理著社會的運行。但是我現在認為不是,中國從來不是一個精英治國的國度。
要分析中國是不是作為一個精英階層統治者普羅大眾,我們首先得定義一下精英主義這個詞的真正含義。精英主義關注社會的權力結構及其特性,早期的精英主義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社會理論,它把社會中的人分為精英與大眾兩種類型,并提供了“精英—大眾”的兩分法。精英主義者通常把社會的上層階層分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他們認為人類的高度文明通常為上層精英所開啟,因為上層精英通常不需擔憂生存問題,而有余力去發展文化活動以致于高度的文化活動從而形成人類文明。
說到精英主義就必須談到大眾主義或者說是平民主義,以大眾主義者的角度而言,常認為精英主義者是蔑視大眾的。甚至認為精英主義是一種蔑視、嘲笑,甚至是仇視普通大眾,認為大眾是一個無知、盲動而又自命不凡的群體的主張,而認為“奴隸”、“野蠻人”、“烏合之眾”、“群畜” 等名詞是精英主義下的產物,事實上,理想的精英主義其實具有一種高道德的自持,關于知識的追求更是無止境的。真、善、美的全面成長應當是身為精英的使命。
所謂平民主義是指把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看做人生真義,并以自身的有限力量來為人類創造美好生活的一種思想。平民主義的特點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以人民的利益作為政策的出發點,提倡少數人的利益必須服從多數人的利益。尤其是,平民主義更加的追求平等,這種平等更多的是經濟上的平等。
然而,在我看來,精英主義和平民主義并不是對立的兩個階層,他們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點或者說都有一些基本的基礎,那就是無論精英主義還是平民主義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他們同時都認為作為一個人的基本自然權利不可侵犯,人的尊嚴和自由不可以被踐踏。他們的分歧點在于,精英主義對于大眾民主和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認為可以的迎合大多數人的利益,會造成對少數人的侵害,形成“多數人的暴政”。而平民主義認為精英主義卻常成為既得利益者作為剝削、奴役中、下層階級的借口,形成一種侵害下層平民的“寡頭統治”。
也就是說,精英階層和平層階層并不是對抗性質、不可調和的,他們的立足點都在于確認個人的自然權利不可侵犯。而恰恰要預防的是精英主義向寡頭主義傾向,平民主義向民粹主義傾向的危險。寡頭主義和民粹主義是不可調和的對立階級。寡頭主義的特征是,國家的存在是為強者服務的,是一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人民得無條件的服從強者的安排,無權反抗。而民粹主義者認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站在人民的立場,并且認為革命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鼓吹激進的革命思想。
但無論是寡頭主義還是民粹主義都沒有個人主義的基礎,沒有個人尊嚴的存在。寡頭主義認為民眾只是統治著維持統治的工具,只是為強者存在的。民粹主義雖然標榜人民的利益,但是這種人民是一種抽象的整體概念,他沒有具體個人的含義,表現了對具體個人的蔑視。所以,一個社會必然要預防這兩種思潮,這兩種思潮的涌現都將對社會的結構、國家的安穩構成極大的危險。
以這樣的定義來看傳統的中國是不是精英統治呢?顯然,我們很明白中國傳統里是沒有個人主義的基礎,也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精英治國的概念。那么,我們傳統的統治是不是寡頭統治呢?也不是,寡頭政治是社會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力受到一個或者多個家族的控制,這些寡頭實際上控制著君主的權力,君主對這些寡頭家族無力可施。中國的傳統是君主專制,權力掌控在皇帝一人的手中,也就是說皇帝的權力不受到其他家族的控制。
中國是一個有著能人治國的傳統,但不是精英治國。我的定義是精英治國必須有著個人主義的基礎,我們國家的古代的科舉考試制度是一種儒家精英的選拔,但是人才的選拔之后并沒有能夠體現一種人文的情懷,而是一種在于“厚黑學”當中摸打滾爬的一條權術之路。
從權力的角度來看,科舉選士制度的偉大不在于它的公正,而在于科舉打通上層與底層之間的通道,使得權力的獲得不再是唯一與血緣相連,使得各個階級開始流動,使得出身不再是唯一獲得權力的唯一來源。底層人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權力的中心,改變自己的命運。科舉不可否認的偉大之處。
然而這種追求幸福的權利仍然是通過權力來實現的,而對于統治者來說,科舉制度不是讓底層人員來分享皇權,只是賜予這些人以某些權力來管理自己的帝國。畢竟對于皇權來說,官權只是一時的,有限的;對于王朝的普羅大眾而言,官員是有限的,微不足道的。
但是中所謂的官吏文化中,是沒有精英主義的成分。官吏的本質,而從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方式來看,統治的模式從“牧羊人—羊”轉變為“牧羊人—狼/狗—羊”的模式。對于只受皇權限制不受人民限制的官權而言,官員對于皇帝只是一條狗,而官員面對老百姓就是狼,狼的本性必然要侵害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官員的本質是貪婪。所謂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皇權的高度集中必然最終導致王朝的沒落,直至被另一個皇權所代替,這就是所謂的“黃炎培周期律”。
正因為“官吏”有著狼的本性,就有著不可根除的嚴重潰敗,使中國傳統政治呈現出周期性動蕩的惡性循環。對官員嚴格的監督制度使官員處于頻繁調動之中,所謂清官文化只是希望官吏成為“狗”,狗確實忠誠,他不會侵犯羊群,但是忠誠的本質是對“牧羊人”忠誠而已。它永遠不會意識到主人的不正當性,也不會意識到羊群有著天然的反抗權。皇帝對忠臣肯定要表彰,但只許自己革命,不許別人革命的改朝換代。
而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信奉的是集體主義,集體主義為專制統治提供辯護。集體主義的核心就是,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個人必須為集體的利益做出犧牲。
在集體主義的含義里,個人沒有存在的價值,也就沒有基于個人之上的上的平等的概念,集體主義的平等是置于集體之中的,是一種平等的、團結的集體主義道德觀,這種集體主義平等觀認為利己、自私是罪惡的,但是它也不是要建立一種仁慈、博愛的平等來代替它,而是以一種共同體的愛來代替,而在這種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組織之愛是難以鞏固、難以持續且不堪一擊的。
這種集體主義的平等觀的特點是,每個人都希望他人都想自己一樣,每個人都是單一的一種模式,他認識自己的復制品,是一種消除個性的平等觀。這種平等還體現在對物質上面的追求,企圖建立一個物質上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在這種經濟平等上的均等觀下,也為統治者社會秩序在社會控制上面提供合法性,要建立一個均等的“大同”世界,也就必須強化統治者的權力,強調集中力量辦大事,只有這樣才能有足夠的財力、物力發展經濟實現“大同”世界,也只有足夠強大的權力資源才能分配社會的財產,建立一個物質上人人平等的世界。
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以及中國官場的權術文化(本質是吳思先生說的潛規則)注定沒有個人主義之上的平等主義以及精英主義,也就無所謂精英治國了。
而與精英治國相對應的我們也沒有平民主義的傳統,我們體現的是百姓主義的觀念。平民主義與群眾一樣站在平民的角度,維護平民的利益,重視平等。但是平民主義有著個人主義的基礎,而百姓主義它只重視平等的程度,它沒有意識到自由的重要性。這樣就會為了得到平等為了獲得安全而放棄自由。然而,沒有自由的保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安全的實現。
這種百姓主義的特征最能體現的就是農民起義上。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從來都是“分土地,均貧富”。這種起義只是人民在殘酷的統治之下以忍無可忍的所爆發出的極端暴力傾向,這種暴力造反的單純的就是一種經濟上的平等愿求,它并沒有想要改變原有政治體制結構。農民的起義總是被迫無奈的也是極其簡單及其淳樸的,然而引導人民起義的所謂領袖打著“分土地、均貧富”的口號推翻原有的王朝,建立起恒久不變的政治體系,重新壓榨新的人民。社會整體的形態是:暴力起義——推翻原專制——建立原有政體的新專制。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巡游經過會稽(今江蘇蘇州),項羽也隨眾人前往觀看。觀望中,項羽不禁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也。”從陳勝吳廣起義之時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無論是劉邦、朱元璋、李自成、太平天國運動以及毛澤東體現的都是這樣的邏輯:皇帝輪流做,今日到我家。一將功成萬骨灰。所謂的偉人、英雄都是建立在層層白骨之上。 我們總是認為喊出這樣的話語體現了這個人宏偉大志和英雄氣概,卻無視這種宏偉和英雄氣概下的那一聲聲冤魂的哭喊。
以太平天國運動為例,它想要建立的是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保暖”的理想社會。我們的教科書上對太平天國的運動是:太平天國,是在滿清統治后期的一次最為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最終被清朝聯合列強鎮壓下去,但是其余部仍進行了斗爭。太平天國前期所到之處都實現了男女平等,廢除裹腳等惡習,女子的地位得以和男子同等,是近代中國民主的開端。《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的革命綱領,突出反應了農民階級要求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強烈愿望,是幾千年來農民反封建斗爭的思想結晶。
但是教科書上沒說到的是,太平天國以平等的名義建立起比歷代封建專制王朝一套嚴格的等級秩序,事實上《天朝天畝制度》,從來沒有真正實施,平等一說更是畫餅充饑,在太平天國他們確實以兄弟姐妹稱呼的,但當哥還是當弟是以官大官小來界定年輕的陳玉成稱其族叔陳得才也為弟,大多出身平民的太平天國的高官,只對下嚴格要求禁欲、禁酒、禁煙,上層什么都不用禁,而且都是最高級的供應。平日里出門,這些人最愛是幾十人抬的大轎,比清朝官員還要擺威風顯闊。
陳致平先生在《中華通史》中對太平天國與洪秀全都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天國的法令森嚴,刑律慘酷,凡犯天條者,一律處死刑。天條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點天燈’‘五馬分尸’‘割肉’‘抽腸’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鳴鑼聚眾,講說道理,宣布罪狀,然后當眾行刑,令觀者驚心怵目,自然俯首聽命,而造成一種恐怖氣氛。這種恐怖統治,完全違背了當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歸于失敗。”
上海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研究認為,太平天國時期從1851年到1865年,經過十四年的戰亂,中國的人口減少了四分之一。太平天國和清王朝都有責任,互相屠殺;太平軍內部還自相殘殺。1856年,洪秀全的天京事變,9月2日東王楊秀清及其“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凈”;9月20日又有兩萬多將士死于屠刀之下;11月2日,韋昌輝和所有姓韋的也全都被殺。
總而言之,太平天國是一個低級的迷信,絕對的暴力集團,是集神權、極權、愚昧一體的統治,只為滿足起義領袖的無限欲望,絲毫不顧及大眾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滿地的荊棘,喪失的生命最少為二千萬至五千萬。
黃炎培道: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
中國是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1944年6月12日答中外記者問)
1949年,我們以為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但是沒想到的是我們還是迎來了一個新王朝。
原創文章,作者:營銷學習社,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kmwhg.com/891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