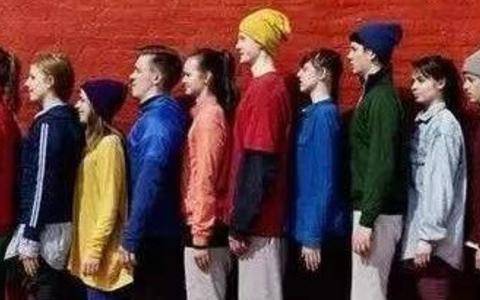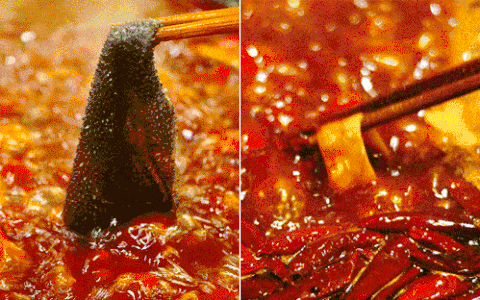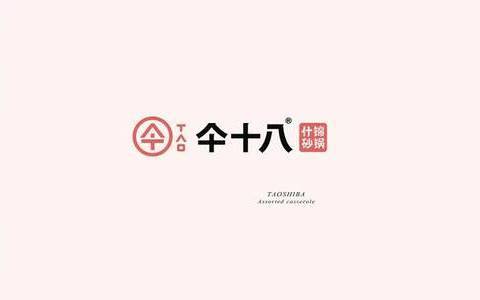這是內參君為您分享的第784期內容;新朋友點標題下藍字或搜索微信號cylbnc關注。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公私合營,讓絕大多數老字號成為國家所有。90年代改革開放,一些老字號后人重新注冊品牌,所以即使同一個產品的老字號,有一些也有了國營與民營之分。 前者也有做的非常好的,后者也有做的走樣的。但更多的情形是,前者的固步自封,盲目自大,讓慕名而來的吃貨們,感到了深深的落差。 這種“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的寥落,以及“我是老號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優越感,對老字號的傳承,無疑是一種不小的傷害。
福建泉州有種小吃,叫做蚵仔煎(閩南語讀:o-a-jian)。蚵仔的學名叫做牡蠣,普通話稱蚵仔煎為海蠣煎。
相傳是鄭成功的發明。
1661年,荷蘭侵占臺南,鄭成功(國姓爺是泉州南安人)從鹿耳門率兵攻入,意欲收復失地。鄭軍勢如破竹,荷蘭軍隊敗退,荷軍一怒之下把米糧都藏了起來。
鄭軍在缺糧之余急中生智,將臺灣特產蚵仔,番薯粉混合加水,和一和,煎成餅吃,想不到竟流傳了一道美食。
▲蚵仔煎
但蚵仔煎可不是臺灣獨有的,在閩南、潮汕等地自古就有了,據說是貧苦社會下民眾的一種創意料理,用來替代糧食的。
對這種歷史悠久的小吃追本溯源是沒什么意義的,只需知道很好吃就行啦。
11月30日,我們到泉州參加“2015海上絲綢之路美食盛宴”。
到達的第一天晚上,歡迎晚宴現場見到了正在炒制的海蠣煎。
平底鍋里,一鍋黃綠相間的海蠣煎冒著熱氣,滋滋做響,煞是誘人。
小份的海蠣煎端上來,綠綠的是青蒜,黃色的是蛋糊,里面隱約透出的是白白的蠣肉。咬一口,蠣肉沒有一點腥氣,那豐美多汁的嫩滑與青蒜的氣息融合在一起,感覺好極了。
這小份的海蠣煎,顯然讓人意猶未盡。
會議結束,去尋找街巷中最有名氣的海蠣煎老店,網上扒拉加沿路咨詢當地居民,得到的結果是:中山南路436號。
我們從西街鐘樓開始走(具體路程可以百度地圖),走得都快吐血了,終于來到了傳說中的中山南路436號。
店面不大,十幾平的樣子,里面擺放著六七張桌子。店鋪的名字叫做“群眾牛肉小點”。
咦,說好的蚵仔煎呢?
進得店里,墻壁上掛著一塊小黑板,上面第一道菜就是蚵仔煎。
店中服務員都是五六十歲的阿姨,當時是下午,沒到飯點,店中只有一個年輕人吃東西。幾個阿姨坐著聊天,說著我們聽不懂的閩南語。
這情形,頗有“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的意思。
古語說得好,大隱隱于市。
中山南路夠繁華,絕對稱得上“市”。在如此繁華的地段,見了這么一個小館子,而且大家都強烈推薦,自然是隱于市的高手。
拿起相機,準備拍門店照片,卻遭到服務員阿姨的制止:“不要拍。”
問其緣由,得到的卻是她喉嚨里發出的咕嚕聲。
蚵仔煎端上來了。
吃上一口,確實口感鮮嫩,內餡香滑。可能走太久,對這道菜的期望太高了,和想象中有些差距。
吃過之后,食記君問了服務員阿姨一些問題,比如這家店什么時候開的,老板是誰,咱們店主營什么,有什么歷史可講等等。
但是,得到的回答也是無一例外:不知道。
有個看似活泛的阿姨多說了兩個字:我們不知道。
店鋪的廚房臨路,站在路上就可以看到阿姨們做蚵仔煎的情形。
食記君舉起相機,做菜的阿姨見狀,張張口,想制止,猶豫一下,卻沒有說話。
廚房門口坐著的一個老伯問:“你是做什么的?”
食記君說明來意,老伯說:“這家店鋪沒有老板,她們是雇來打工的。好像是……某個餐飲公司的吧,我也說不清。”
做菜阿姨往平底鍋里打了五六個雞蛋,用鍋鏟攪和了一下;往雞蛋上加了兩勺海蠣肉,翻炒一會兒,將帶著蒜苗的稀面糊倒了上去。
▲右下角桶內是混合著蒜苗的稀面糊
食記君問:“阿姨,為什么不用韭菜?海蠣煎不是要用韭菜嗎?(海蠣煎通常用韭菜)”
阿姨終于開口了:“這個季節哪來的韭菜。”
又問了好幾個關于做這道菜的問題,答案都是沉默。
天曉得為什么會這樣,難道是打開方式不對?
我們見再無收獲,付了錢就離開了。
真是一次失敗的行程。
食記君后來走訪了一些泉州當地的餐飲人,得知“群眾牛肉小點”原是國營,改制以后,承包給了個人。
如果一個人的肝有問題,那么他的眼睛肯定看不清;如果腎有問題,他的聽力就會受到影響。
內臟之病,只看外表是很難看出的。
但是,疾病的癥狀必然發作于人們所能看得見的地方,只不過是潛伏期長短的問題。
國營是酒,民營是水。
朋友聚會,招待客人,要喝酒;勞動結束,口渴難忍的時候,我們要喝水。
兩者功用雖然無法相提并論,但是摻了水的酒就令人不快了。
在服務業,如果摻了水的酒還抱著自己是酒的態度,終有一天,會被水所替代。
來源:好食記
作者:張冬冬
統籌:劉曉紅
編輯:閆太然
視覺:陳曉月
原創文章,作者:餐飲老板內參,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kmwhg.com/1442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