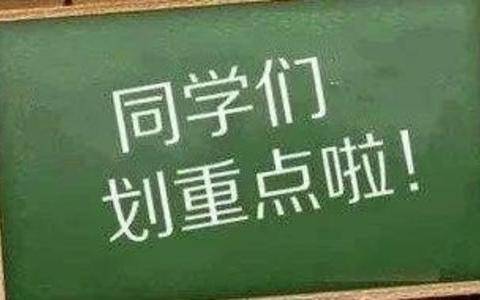▲ 席剛參加第十二屆戈壁挑戰賽。4天時間里,戰高溫、斗沙漠、征戈壁,完成沙漠徒步120公里。
他和新任總經理、財務經理組成了領導小組——這不是第一個試圖挽回子公司頹勢的領導團隊,但他們是第一個讓它扭虧為盈的團隊,并且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看起來他們運氣不錯,對嗎?
事實很快證明這不是巧合。
25年前的一則廣告改變了一段人生軌跡。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1994年,大學畢業生席剛被《四川日報》上的一則招聘廣告留住目光,主動跑去遞了簡歷。
一番常規的面試問答后,席剛忍不住問對方:“你們這個企業到底怎么樣?”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民營企業生命力蓬勃,年輕的席剛想要靠近卻又猶豫:企業的管理規范嗎?信得過嗎?
面試負責人答:我們老板講,企業財務一定要真實。
席剛信了,他覺得企業的底線守住了。25年后,席剛在漫天大雪的天氣里回憶這一細節時笑說:“因為這句話,我托付了自己。”人的命運永遠與時代交契。
他應聘的是中國首家民營企業集團、當年中國500家私營企業排名第一的希望集團。1997年,該集團經歷組建,成為人們熟知的“新希望集團”(以下簡稱“新希望”),老板是劉永好。
用席剛的話說,自己當時去了一個“很火的部門”——人力資源部。他負責招管理層、也需要招基層員工,“總經理、保安、廚師,全都招”。急速發展壯大的新希望不斷收購、兼并、投資、招人、擴工程,規模效應彰顯,人力缺口巨大。席剛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使出了渾身的本事,識人知事。歷練兩年后,席剛被調去集團下屬一家虧損子公司做辦公室主任。這個機會是席剛主動爭取的,因為他想走得更遠,就必須通過基層鍛煉——這個機會很重要。
他和新任總經理、財務經理組成了領導小組——這不是第一個試圖挽回子公司頹勢的領導團隊,但他們是第一個讓它扭虧為盈的團隊,并且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看起來他們運氣不錯,對嗎?
事實很快證明這不是巧合。做了兩年辦公室主任后,席剛被調到四川達州一家面臨虧損的面粉廠做辦公室主任,而后升任總經理一職,他笑言“自己使出了十八般武藝”,再次扭虧為盈,在面粉銷售向市場全面開放的1998年,連續3年利稅超過1000萬。
人心
席剛的經歷背后藏著新希望的發展思路。2001年,新希望開始進軍乳業板塊。隨后十幾年時間內,新希望乳業先后整合了多個區域數一數二的品牌:四川華西、安徽白帝、杭州雙峰、云南蝶泉、昆明雪蘭、蘇州雙喜等十余家地方性乳制品企業。業內評價新希望乳業意在通過并購整合的方式從一家區域乳企成長為全國性的城市型乳企聯合艦隊。
這條路非常難走,從某種程度上說,并購一個品牌比新建一個更難,兩種體制的沖突、融合讓整合盈利的難度陡增。據一些國際知名研究機構、咨詢公司的調查結論,國內企業并購的成功率僅僅三成左右,可見并購后成功的難度之高。“就像結婚,兩個人要學會相處,我覺得挺好玩的,但很累。最大的問題是怎么轉變這些老員工的觀念。”席剛管理過多個合資公司后,學會了尊重并購企業的既往歷史、文化和原有團隊。
“企業整合首先整合的是人心,其他都可以放在這個之后。”經過幾任團隊摸索,新希望乳業終于摸索出一些有效的辦法,方法真正接受檢驗是在云南。
2008年,在新希望乳業擔任副總裁的席剛被調派到云南兼任片區總經理,管理蝶泉和雪蘭兩個兄弟品牌——在國企改制、企業虧損的現狀下,還增加了“品牌面臨同區域競爭”的難度設置。更大的磨難是席卷全國的“三聚氰胺事件”,當時席剛到云南履職僅2個月,消費者對國產乳制品的信心跌至谷底,產品銷量大跌。
質檢機構很快進入企業,結果是新希望乳業的多個品牌均未檢測出三聚氰胺。席剛內心坦然,很快在云南發起“透明工廠計劃”,邀請媒體、消費者、經銷商參觀牧場、了解產品加工過程。3個月后,銷量不降反升。“透明工廠計劃”隨后復制到整個體系并不斷升級,“迎進來”“走出去”相結合,提振消費者的信心,也不斷倒逼產業鏈做到精益求精,這一做法效果顯著,一度經營困難的兩個品牌如今成為新希望乳業的一面旗幟,而“透明工廠計劃”也發展成為今天的“食育樂園”“透明工廠+生態牧場游”等一系列沉浸式體驗活動。當人們真正富有才華的時候,運氣并不是那么重要。
云南片區的成功,讓劉永好眼前一亮,他把席剛調了回來,希望他用云南的經驗把整個平臺都做起來。2010年,席剛從云南回到成都,擔任新希望乳業總裁。“無論是劉永好董事長還是劉暢董事長,都給了充分的信任和高度授權。”席剛敬重劉永好的學習能力和學習精神,他認為團隊始終保持進化狀態與此密不可分。
回來后的席剛常跟總經理們講:作為核心管理層,讓企業健康良好地盈利,代表一種能力,也代表職業經理人的尊嚴。2013年,新希望乳業的子公司們全面扭虧,甚至出現了比較好的盈利的公司。
一眾高管、總經理們,都在乳業干了近十年,養出默契,成了“好搭檔”。有同事評價席剛為人親和、情商高,“他跟你聊天的時候,你會覺得很愉悅、很開心,覺得他很懂你”。這種溝通方式得益于他換位思考的習慣,他會從對方的出發點去了解對方想要什么。
“從基層的員工,一直到中層、高層,沒有人說他不好,都很喜歡他。”一位和席剛一起工作超過10年的老同事認為這是新希望乳業高層團隊穩固的原因之一。
▲ “很多事一定要多嘗試。”席剛不安于現狀,想走得比變化更快。在他看來,成功的原因極其相似,失敗的原因各有千秋。
反對
席剛在辦公室待不住,他喜歡走市場,有時候叫上個同事一起去,有時自己去;跟經銷商聊、跟消費者聊,也跟促銷員聊。“他喜歡Marketing(市場),一走市場心情就很好,無論好壞,任何反饋都可以,都會讓他覺得心里更有底,更安心。”新希望乳業市場總監張蕾描述席剛講市場時的場景,“他滔滔不絕,會講得越來越興奮。”
通過深入市場,席剛抓到很多靈感,比如新希望乳業現在的旗艦產品“24小時巴氏鮮牛乳”,產品基本上從生產到下架的時間不超過24小時,不售賣隔夜奶,限時只賣當天。靈感的源頭是一個供應商跟他聊起“庫存”話題和煩惱。席剛腦中似乎有什么東西一閃而過:經銷商和消費者都對時間非常敏感……一款不需要退貨的產品……
當他抓住“24小時巴氏鮮牛乳”這個想法時,立刻打電話通知下去要做產品設計,并首先在成都試點。結果他最好的兄弟朱川跳出來激烈反對。“只賣當天?所有人第一想法是訂單怎么做?賣不完怎么辦?”朱川說,“因為先在四川做,所以只聽到了我的反對聲音,如果在所有子公司做,所有公司都會反對的。”
朱川從云南開始一直和席剛做搭檔,現任新希望乳業總裁。2011年,新希望乳業做24小時產品,加工技術和奶源上是成熟的,難點在于供應鏈和訂單管理,倒逼著企業以小時為單位去安排工作——平時的低溫奶會賣7-15天,工作以天為單位安排。
朱川的極力反對并沒有說服席剛,24小時產品必須做。朱川承認自己這次“服從多于理解”,出于多年配合的默契,盡管不服也愿意相信席剛,“我覺得一定有他的道理”。可是24小時產品的概念在當時的消費習慣下略顯超前,市場沒有立刻回報以笑臉,訂單耗損比例高,企業承受重壓。晚上9點,席剛自己跑去商超把當天沒賣掉的24小時產品送給路邊市民,“這是我們的新品,請品嘗。”牛奶很快就送光。
慢慢地,大家發現這是一條對的路,競爭對手也開始跟進“24小時產品”了。于是新希望乳業旗下的其他公司也開始快速復制,幾年后,又推出升級版的“黃金24小時”,只選取生態自營牧場生產出符合“中國優質乳工程”要求的優質鮮乳,這些優質原奶將在全程冷鏈的條件下運抵工廠,以全球領先的72℃,15秒的殺菌技術進行低溫殺菌,確保營養物質的充分保留,其活性營養物質達到同類產品的三倍以上,這款產品成為新希望乳業“鮮戰略”下的金牌產品。
“回過頭來再看,這件事對整個供應鏈的建設和團隊建設的幫助很大,如果我們能賣只賣一天的產品,那么5天、7天、21天產品訂單的準確性、物流的規范性,統統都提高了。”朱川不后悔曾經的“反對”,因為真理越辯越真;等2018年推出“黃金24小時”升級產品時,他積極推動項目。這次對席剛的理解遠大于服從。
24小時系列產品凝聚了新希望乳業磨礪多年的“芯科技”——數字化可追溯的自動化牧場、先進的乳牛飼養技術、國內僅有少數企業掌握的“72度”超低溫殺菌技術、領先國際的檢測指標、可實時追蹤的智能冷鏈體系……
張蕾打心底里佩服席剛對于市場把握的敏感度和精準度。24小時產品推進初期的強大阻力,反而成為席剛市場前瞻性的重要印證。“這樣的人就很能拿捏得住下屬”,張蕾認為這是乳業上下服他、愿意為實現大目標披肝瀝膽的原因之二。
席剛自己有另一個看問題的角度:“要去做一些有挑戰、有難度、短期內大家也不那么看好的事。因為好做的事,我們已經沒有機會了。”
▲ 席剛出席“第六屆中國好鮮奶·新鮮盛典”。有行業數據顯示,國內鮮奶一年總銷售額達到120億,數量約10億盒,可裝滿502個國際標準泳池。新希望乳業2010年提出的“鮮戰略”,被一步步驗證為是正確的。
承諾
2010年,席剛成為新希望乳業掌門人,當時除了云南子公司,其他全都虧損。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席剛還是向總經理們畫了個餅:“我們兄弟一起,上下同心,爭取努力幾年,把這個平臺做成一家優秀的上市公司。”
老員工當時心里不信,覺得天上不會掉這種餡餅。
然而,2013年新希望乳業全面扭虧;2019年1月25日,在深交所上市,股價連續多日漲停,目前總市值超過光明乳業。
席剛很冷靜。等到上市敲鐘后的第二天晚上,他才發朋友圈說:“十年磨一劍,兌現了一個承諾,練就了一個團隊,跑出了一個模式。新乳業,新起點,新未來。感恩大家!”
這其中,模式指的是“1+N”聯合體模式,通過并購、聯姻、整合區域型乳企,實現了以一家母公司、統一管理運營體系為改革創新核心主動力,為全國N個傳統區域型賦能,協同前進的共同體。“收購的十幾家公司沒有一家虧損,都盈利。這件事,比上市讓我更有成就感。”席剛說道。
多區域、多品牌的分布,讓新希望乳業每個區域都面臨巨大壓力,這刺激他們對市場變化極其敏感,只有把產品做得更新鮮、更快捷、更貼近當地用戶的需要,才不會成為“溫水中的青蛙”。
朱川深以為然。新希望集團有一份《經理人行為準則》,他對其中一條感觸頗深:“發自內心的歡迎變化,因為機會蘊藏其間,更重要的是保持對變化發生的敏感,敏感度是管理人員的水平儀。”
席剛反復強調“創新”,要“因變而變”,新希望乳業的整個節奏被他帶了起來,完全不是一家“巴適”的成都企業,他要求月月有興奮點,這樣才能保證不落伍。另一方面,席剛又不怕友商跟進,無論是香蕉牛奶、24小時產品、還是初心酸奶,市場跟風者眾,他不太在乎:“好的東西總是會有人跟進,這證明了創新是有價值的,推動行業進步嘛。”
根據上市公告顯示,新希望乳業本次募集資金扣除發行費用后將用于安徽新希望白帝乳業有限公司搬遷擴建項目、營銷網絡建設及品牌推廣項目、研發中心建設項目、企業信息化建設項目。
席剛希望打造“非傳統乳企”,通過科技手段解決企業的痛點、提高競爭力,讓企業更有效率、更好地服務消費者。通過科技的投入,解決產品可追溯的問題、工廠智能化甚至無人化的問題、實現消費者在云端360°被滿足。
▲ 2019年1月25日,新希望乳業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正式掛牌上市。劉永好、劉暢、席剛、朱川等人一起在現場敲鐘。
上市兩個多月,新希望乳業市值翻了3倍不止,受到資本市場關注。2019年春節后的開工會議上,席剛要求總經理們“忘記股票”,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把公司變得更有價值,把公司做得更優秀”上。
在新希望乳業,大家依然靠業績說話,企業內部設有“紅黃牌制度”,針對子公司總經理的年度績效目標,進行每季度評比。業績不達標,則拿黃牌警告一次;連續兩次黃牌則被紅牌懲罰降級,執行嚴格。“好像除了我,大家都拿過牌。”朱川回憶說,“拿到紅牌真的會給你調崗、降級。曾經有個總經理拿到紅牌后在朋友圈發了5個字‘人生第一次’。”事關尊嚴,不得不全力以赴。
降級不是永久性的,如果連續兩次評比優勝,又能“官復原職”——大部分被罰紅牌者又自己贏了回來。即便如此,最快復職也需要半年時間。起起伏伏間,誰也沒甩包袱走人,“2010年到現在,總經理沒有一個離開。”席剛覺得大家很給力——跟他想的一樣。
朱川清楚記得在一次總經理會上,席剛講“什么叫兄弟”,他說:“業績上能夠相互支撐,才是做兄弟的前提。”
中國第一家專注于餐飲供應鏈的自媒體
筆者擁有十余年豐富的大宗農產品期現貨研究、餐飲食材采購和冷鏈物流等食品供應鏈的實踐經驗,是英國皇家采購和供應學會五級認證會員,餐飲供應鏈和新零售生鮮變革的長期觀察者,多篇文章發表于今日頭條、億歐網、餐飲老板內參、掌柜攻略、《冷凍雜志》和《中國食品報》,曾在掌柜攻略旗下的【勺子課堂】直播講授供應鏈公開課《餐飲的采購和供應管理》
曾為以下品牌提供供應鏈解決方案:正大食品、新希望六和、鳳祥食品、辛普勞、安德魯、易果生鮮、寧夏悅豐、北京宴、香港馬會、吉野家、田老師紅燒肉、美團快驢、鏈農、優配良品、Pizza Express、華萊士、臺滋味、瑪格利塔比薩、日昌、云海肴、楊記興臭鱖魚、蜀海、四季明湖、明湖小樓、半天妖烤魚、董小姐愛地鍋、望京小腰、焦耳外賣等,致力于幫助餐飲食品企業提高供應鏈管理水平。 餐飲供應鏈探討:文武 13401153561 (同微信)
原創文章,作者:餐一謀,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kmwhg.com/195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