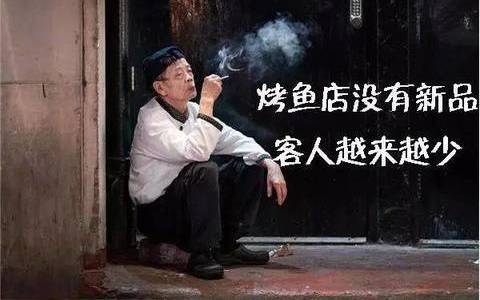尹江波談開店:“每開一個店就要成一個店,一定要創造利潤。”
秦朝:這半年疫情對陶陶居的影響大不大,現在恢復的情況怎么樣?
尹江波:疫情不僅對陶陶居,對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餐飲都是一個重擊。好在我們上海的門店位于黃浦區,允許堂食,所以沒有關過門,那個店還不錯。
在廣州的門店停止堂食也就10天左右,我們在每一個區都是堅持到最后一個停止堂食的。關閉堂食期間,我們也做了團餐、外賣等業務。做這些事情對餐廳的運營來講,并不見得有太多收益,要是不允許我們經營,餐廳可能一個月都頂不下來。
受疫情影響,陶陶居上半年的營收少了一個多億。2月份基本上沒有虧現金流,3月份開始有現金流回來,4、5、6月份慢慢一步步變好。
我們每年開店不多,計劃開6—8個店。這是去年或者前年已經簽好的,我們不能違約。上半年是動不了,下半年要把簽約的這些店開出來,所以下半年的任務非常重。
目前來講,陶陶居還沒有恢復到去年同期水平,但基本上也接近了,在9成以上。
秦朝:如果按照這種進度的話,到年底跟去年預期的目標會持平嗎?還是會有差異呢?
尹江波:這次疫情對我們發展布局沒有任何改變,我們目前的能力是每年開6—8個店,今年計劃在廣州、深圳、上海、北京四地開新店。
因為我是一個跑馬拉松的,也是一個長期主義者,不會說市場好我們就加快速度開。上海所有好的商場都在跟我們談,今年、明年的開店計劃我們都已經滿了,現在在談2022年的。企業整個發展也并不快,但是每開一個店就要成一個店,我們一定要創造利潤。
我比較尊重的餐飲企業,香港的利苑就很穩定,澳門的金悅軒集團,每開一個店,都經營得特別好。比如它在珠海的一個店,有46個房間,一年的銷售額3-4個億,每天的營業額上百萬,一個店營業額可以堪比上百家小店。這一點確實值得我們思考,我們是做規模,還是做單店的效益。
尹江波談中式正餐:“它離不開手工,如果非要做標準化,非要建工廠,那是逆勢而為,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秦朝:從數據上來看,大家一直在反映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餐飲連鎖化率不到5%,非常低,大部分餐飲企業都是單打獨斗的狀態。同時有一個問題,就是說中餐里面很難出現海底撈這樣的巨無霸連鎖企業。
中餐的發展到底該以什么樣的路子發展,是像西餐那樣走連鎖規模化?還是像陶陶居這樣穩扎穩打,每一家店的產值很高,利潤很高,這種方向?
尹江波:這個問題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我們可以學習麥當勞、肯德基的西式標準化,主要是看品類。像火鍋、快餐、茶飲這些品類,標準化程度就可以提高到80%—90%。標準化程度越高,意味著會有工業化,有工廠做支撐,有了工業化做支撐才有規模化的發展。所以要解決標準化、工業化、規模化的問題,西式快餐是建立在這三化的基礎上,所以它可以全球發展。
中式正餐的特點是什么?本質是什么?
我認為中式正餐永遠不要跟資本結合。因為我走過這一段路,2011年11月16日我是拿到最早的一批風投,當時投了8千萬。2012年,我感覺走不下去了,就跟機構談把股權全買回來。那時候我建了中央廚房,來降低門店的人力資源成本,降低對技術、師傅的依賴。但是后來門店的業績大幅度下滑,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因為東西不好吃了。
那是我在經營企業過程中最焦慮的時候,資本投了你它是有周期的,大家約定的5年要上市,當時計劃在香港上市。走了一年半,我說再這么下去人會死掉。2013年3月31日,我一次性把股權全買回來了,買回來以后我就覺得誰也不欠了,壓力瞬間就釋放了,當然那時候也是關了很多門店。
即便背上了很大的債務,但是人是輕松了,人輕松了會安靜地思考該怎么做,要不然就會一直在焦慮之中。2013年我先把股權問題解決了,解決了公司架構問題,開始琢磨怎么做陶陶居。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我們2015年開出來第一家店,因為你經歷過那些,你知道哪些可為與不可為。
我們必須尊重中式正餐的本質,它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家有各家的味道。因為它離不開手工,非要逆勢而為,把依靠手工的,依靠技術與師傅的,非要做標準化,建中央工廠,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中式正餐依賴手工,每個師傅處理的口味不一樣,其實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為什么要一統天下呢,統不了。
秦朝:這些年,中餐標準化得到了很大發展,“去廚師化”似乎已經成為很多餐飲創業者的共識。但是今年以來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昨天巴奴毛肚火鍋的杜總也在說,去廚師化其實是很危險的。就像剛才尹總說的中式正餐的本質就是百花齊放的、離不開手工的,如果我們硬要做一些工業化的改造,那可能就是逆勢而為的。
這讓我聯想到前幾年的中式正餐,比如說俏江南、湘鄂情,有很多中式正餐企業跟資本聯手之后,并沒有很好的結果。最近十幾年來一直在做中餐標準化的一些頭部餐飲品牌,比如說外婆家、西貝、九毛九,也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現象,就是大家在中式正餐的板塊其實好像都在放緩,甚至在停滯。
外婆家吳國平也提到,這個品牌接下來不會做大幅的擴張,因為它是中式正餐的業態。他會寄希望于老鴨集這個偏快餐的品類。
這種現象在西貝身上也有,西貝正餐這個業態在過去幾年經歷了高速的增長,比如說到了500家店,但是很明顯今年,甚至未來兩年沒有太多的開店計劃。賈總也在嘗試一些快餐,我們暫且不去討論他們為什么去做快餐,我覺得一定是做規模化考慮。
九毛九的市值一直在增長,這兩年拉動它增長的主要是太二酸菜魚這樣一個單品品類。眉州東坡的正餐部分其實也在放緩,現在也發力零售板塊。
你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以往靠中式正餐起家的這些頭部的品牌,中間經歷了中餐標準化的歷程,也經歷了連鎖規模化歷程。但是好像又回到了剛才尹總2012年預測的那個樣子。
這樣綜合起來看,確實會令我們反思,中式正餐的道路到底該怎么走?這個問題可能需要我們持續花時間探討,它確實會影響很多東西,包括大家熱議的去廚師、標準化、工業化的方向是不是真的要發生改變。
尹江波談老字號:
“最好的傳承一定是與時俱進。”
秦朝:接下來想討論一個關于老字號的問題,陶陶居是一個140年的老字號,但是我們也看到這兩年有些老字號過得其實并不好,比如北京的全聚德、天津的狗不理,甚至有些老字號還在倒閉,在消失。
這其實也是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很多餐飲人起初都夢想著做一家百年老店,但是那些已經有上百年歷史的老字號在當今這個環境下卻遭遇這么大的逆境?我想請同是老字號掌門人的尹總談一下為什么這些老字號會出現這種情況?
尹江波:點評其他老字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其實不敢。我只能說,什么叫老字號?好像一講老字號就代表傳統,我們要寫一個大大的NO。
我們要看時尚界那些最牛的大牌是什么?比如路易威登(1854年)、愛馬仕(1837年)、香奈兒(1910年)、古馳(1927年)等等,他們是不是都是老字號?他們在干什么?他們在引領時尚潮流,所以說老字號不等于傳統。
正是因為它有很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所以它能枝葉繁茂。關鍵是我們怎么讓它枝繁葉茂,如何引領時尚和潮流?
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的需求在發生改變,不僅要吃飽,還要吃好、吃健康,這其實就是潮流,就是時尚。
最好的傳承一定是與時俱進。什么叫頭部企業?頭部企業不是看規模,而是在這個行業的領軍地位,能不能引領這個行業。
世界級的那些老字號都在引領潮流。靠什么引領?就靠與時俱進的創新能力。
古馳一度下滑很厲害,因為它的創新能力在下降,后來換了一個新的設計師,創造了完全不同的風格,一下子又起來了。
我們對這些時尚的追求,這兩天我看朋友圈發的帖子,說是經濟不行了,還是你自己的經濟不行了?配的圖就是那些奢侈品在排大隊。其實人們對時尚,對潮流的追求一直在。
我們餐飲業如何像服裝這個傳統行業一樣,也做成我們的時尚業?哪些要創新?創新不是說把餐廳搞得全是涂鴉,搞工業風,也不是搞雜耍之類的,什么都有,這就分不清主次了。
我們看大牌的老字號是怎么玩的?他們玩的是非常專業的。比如說LV最早是做箱包的,然后一步一步做起來的,但是LV最強大的基因依然是它的包包。香奈兒做香水,雖然也做了珠寶、服裝,但它的香水依然有名,比如說你去買香水,我們在化妝品店或者專柜,它是非常專業的,它一定要有跟它的東西匹配的環境,而不是說我一個有文化的餐廳,就把所有的文化往里裝。我們要理解一個品牌它背后的基因、故事是什么,在傳承發展的過程中不要離開這個主線。
尹江波談陶陶居:
“重的人力資源就是護城河”
回到陶陶居,它就是喝早茶的地方。喝早茶是什么?它是廣州人的生活方式。所以陶陶居輸出的是廣州人的生活方式。
我說上海沒有一家真正的粵菜。雖然利苑、翠園、稻香有在這里開店,但這是港派粵菜,這和廣州的粵菜不一樣。出品有很大的差異,廣州粵菜對食材的追求不一樣,雞必須要當天晚上殺凌晨用。雞有雞味,魚有魚味,講究食材的新鮮。為什么粵菜走不出去,是因為食材很難走出來。
在上海開店,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先找供應鏈。在上海開一家800平米的店,用135個員工,90%的員工是廣州派來的,服務員的工作語言也是粵語,這是一個整體文化的輸出。
以前一般在其他城市做粵菜的餐廳,都是聘請幾個粵菜師傅過去,到當地再招一些本地師傅,這樣的組合可以降低成本。成本降低了,但出品是騙不了的。
我們不是這么做的。我跟團隊講,我們慢慢開,每開一個店一定要旺。事實證明我們目前19個店,通過商場提供的數據,我們每一個場子坪效、人效都是第一名。我們800平方米,可以做到600萬以上的營業額,客單價就100多塊錢。
不過我們的人工成本非常重,一般開800平米的一個店50—60個員工就夠了,但是我用了兩倍多的員工,又是從廣州派到上海的,所以成本極其高。
以前有同行來廣州參觀,看完以后說學不了,因為不敢用這么多人。我們的出品是不偷工、不減料,手工一定要用人手慢慢去做,服務也是有足夠的人手服務才好。我們重的人力資源就是護城河,這就是藍海。所以我們到哪里去開店,我們并不會考慮有沒有其他做餐飲或者同品類茶點。
我們不會考慮競爭,是來自于我們對出品,對我們自己團隊的了解,所以我們并沒有懼怕競爭,也沒有放緩我們發展的腳步。
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一個老字號陶陶居怎么做到?我說了我永遠是一個產品主義,出品不好什么都別談。出品怎么好?就是食材加廚師手藝。
我曾經煙臺開了一個海鮮店,當時也有粵菜,師傅出了一波又一波,怎么做都做不好,后來從食材、干貨、醬料上找原因。
我們在山東采購粵菜用的醬料80%都是假的,跟我們在廣州用的不一樣。所以廚師怎么做出好的東西,食材非常重要。比如金悅軒對食材的要求是非常極致的,所以它的消費是高,高的有道理。
為什么會有餐廳會倒閉?這個問題要反過來問,好吃的餐廳有倒閉的嗎?好吃的餐廳一定不意味著便宜,食材好就貴,物美價廉是一個悖論,應該是物美價貴。
尹江波聊管理:“我只看現金流,無論這個店成本投入多少,就是三個月不能虧現金流。”
秦朝:剛才中間也聊了很多陶陶居的戰略,護城河確實很深,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餐飲或者中小的餐飲企業確實很難去學習陶陶居,因為陶陶居確實學不會。
尹總能不能站在行業的角度,再結合現在的環境給我們絕大部分的中小餐飲企業一些建議?
尹江波:
1)方向比努力重要
我的企業也是由一個小店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企業發展22年了,1998年10月22日創業,從13張臺的山東老家一步一步做起來。大企業一定是從小企業、中企業走過來的。
我比較喜歡這樣一句話:方向比努力重要。當一個方向對了,你的每一步都是一個累積,但是你方向錯了,就是一會兒東,一會兒西,到最后什么都沒有。
我們第一個企業是山東老家品牌,是一步一步成長的,當然重點差點走了岔道,但是我們及時回來了,依然回到產品的本身。因為我們是做中式正餐的,不可以跟資本結合,也不適合做過度的規模化。比如說我們開10個、20個店,再開多可能管理、出品就變得不可控了。
2)考核指標:現金流
對我來講,其實我沒有苛求什么企業戰略,陶陶居一定要開多少店,我在開的時候總部的高管都有投資權,每一家店的店長對其他店都有投資權。首先是看團隊愿不愿意開,第二有沒有能力開,如果達成一致,我的要求就是考核指標。
我們集團有很多產業,餐飲只是我們其中一個餐飲,還有茶葉、生物科技。我對餐飲事業部的要求非常簡單。我只看現金流,無論這個店成本投入多少,就是三個月不能虧現金流。
我們要專注餐飲這個領域,就老老實實把產品做好,消費者會買單的。把產品做好,把環境匹配起來,服務不要出大問題。然后就是價格合理,一定不能打價格戰。
客單很重要。陶陶居為什么會有創新,是因為它確實能賺到錢。為什么賺到錢?客單價非常重要。外婆家、綠茶60、70塊錢的客單價,讓全國很多餐廳都感到很大的壓力,因為它的利潤很薄很薄,如何請優秀的師傅,如何創新?陶陶居廣州店的客單價就是100—120元,上海就是150元的客單。有了客單,我們的利潤空間就會好,反過來可以支付各方面的成本,我們也有資金投入創新。
3)組織架構、權責清晰
我是非常追求規則的一個人,我到每一個店,哪怕喝一瓶水都必須現金買單,我們公司任何私人宴請,沒有任何人有權力簽單,游戲規則是非常清晰的,責權也非常清晰,就不會那么累。
有朋友問,我每年跑十次馬拉松,還開那么多店,做那么多品牌,還有茶葉工廠、醫療的投入,時間是怎么分配的?我說是因為這是團隊做的事情,分權分利分責。
組織架構、責權要非常清晰。這樣我們就能調動更多的人,而不是只會說我的愿景是做百年老店,那是你的愿景,跟員工有什么關系?我們做的事情是跟他們有關系,是他們要做的。
真真 18037518262(同微信) 栗軍 13718277715(同微信)
原創文章,作者:餐飲老板內參,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kmwhg.com/151274.html